近日有香港朋友透過春山出版社聯繫我,並提出一些涉及香港、台灣和寫作的問題讓我回答。我把那些很重的問題揣在身上,帶來帶去好幾天,不時與先生討論幾句,且一面隔海遙望香港,一面回溯記憶之河,掬取出靈光碎玉般的片段,先寫下來。片段引出片段,成文如此:
在漫漫的時間之流裡,如果能夠知道此時此刻,我們置身於歷史發展的哪個階段,接下來可能會遭逢什麼際遇,心會比較安吧?上世紀七零年代我在台中讀大學的時候,同學私下瞎聊說我們這時候大概是「偏安南宋」,再有段歌舞昇平的日子應該沒問題,又有說或許是在「明鄭」時期吧,不定什麼時候清廷就跨海打過來了。幾個女生那時候臆測這些其實有些危險。幸好無事。而我們也只是說說,並沒有多麼不安,因為日子還是好好的如常過著。
多少有些不安的大概是我們的父母親,他們從不聚眾談論這些,不過外省籍的回想四零年代渡海而來的悲傷往事還歷歷在目,本省籍的憶起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仍然心痛難平,而白色恐怖的陰影未散,依舊盤繞在社會上空。但願不再打仗,不必逃難,不會出事,子弟若善讀書,有辦法留洋出國,本省籍、外省籍的父母都支持,能夠拔腳離開泥淖般的政治環境,此後安心多好。
時至2019年,香港石破天驚爆發反送中運動,在各界民眾艱苦奮鬥的過程中,時有年輕朋友的拘捕、傷亡事件傳出,隔海聽聞亦哀傷無已。十五歲的游泳好手陳彥霖赤裸浮屍海上後,我認真在網上反覆觀看校方公布的閉路電視影像中,她在學校走廊、電梯等處徘徊的最後身影,想看出影片中的她是何狀態,又因為有人放出照片說影片中的陳彥霖不是真的陳彥霖,我便來回比對,想找出是或不是的蛛絲馬跡。當時,有朋友拿香港和台灣相比,認為香港像是處於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的關鍵時期,若能忍過陣痛,衝破瓶頸,或有可能跨出一大步,贏得民意伸張的未來。雖然很希望真能是這樣,但在陳彥霖浮屍、周梓樂墜樓等多起年輕人死因不明的痛事皆被歸類為自殺事件之後,我腦海裡浮現二二八事件當時眾多無名屍體浮沈基隆港,血染淡水河的淒慘影像。
陳彥霖和周梓樂的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明死亡的香港,相當於發生美麗島事件時的台灣嗎?我不覺得是,當然那可以是期望。實際上香港與台灣不好相比,畢竟二者曾有過很不一樣的過去,走過很不一樣的路。
1936年出生於香港,並成長於香港的故友唐文標教授,生前曾提到說殖民地香港沒有人碰政治,他的父祖輩無一談過或關心政治,政治與他們無關,他們亦無從著力政治。
在香港,你不碰政治,政治也不碰你,幾代人的心力自然會放在通商、金融、藝文、娛樂、教育等方面。在這些領域,香港人都開拓、發展出蓬勃的成果,一直閃耀至今。隔海生活的我,也品嚐著香港的果實成長而不自覺。從小到大,我看過許多香港出品的電影,電懋、邵氏的明星太熟悉了!電影乘載的人情世故、風物光影,一併囫圇吞下。我小時候的重要讀物是母親幫我訂的,香港發行的半月刊兒童刊物《兒童樂園》,那份在1953年創刊的雜誌含帶中國文化的底蘊,富藏世界各國的精神與知識養分,且敘事、表現手法豐富多元,長大回頭看,方知我是那樂園裡出來的孩童,身心情意皆受薰陶、滋養,且由此建構了初期的世界觀,例如我知道現在這個滿佈人類的世界曾經是各種恐龍的世界,曾經是劍齒虎和猛獁象的世界;我也知道美好的城市與文明可能一夕被毀,偉大的龐貝城就被埋在火山灰下,好多年後才給挖出來。
香港人不碰政治,因為沒有參政的權力。不碰政治也可以活得很好,因為政治不碰你,而且香港在英國治下是很成熟的公平法制社會,人有機緣,有本事的話,甚至可以由底層翻身,直翻好幾層。蘋果日報和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香港給他機會,讓他一個十二歲由廣東偷渡香港,出離共產黨政權的窮小孩闖蕩出一番事業。而黎智英與其他香港成功企業人士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只做生意,經營媒體,他還碰了政治,用很大的力道碰了政治,以致七十二歲成為共產黨的囚徒。他在2020年出入囚牢的艱困時日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這裡,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歸功於此地的自由。或許,現在是到了我回報這一自由的時候了。」
2021年他的獄中書這樣寫:「香港的情況越來越令人心寒,正是這樣,我們更需要自愛和珍重。時代在我們面前既倒,更是我們昂首站立的時候。請同事們保重。」
這是直面事實,讓很多人心痛、流淚的話語。我很期待有一天,香港重得自由的時候,香港有比較健康的政治環境的時候,可以拍出他的故事。
回頭看台灣,台灣人的經驗與香港不一樣,幾代積累得知:你不管政治,政治就會管你。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的精神徹底被按入泥濘,進入白色恐怖罩頂的漫長黑夜。可是,即便父祖一再交代決不可碰政治,那決不可碰政治的理由卻在很多後輩心中騷動、琢磨、轉化,引生對話與質疑,於是他們參照現實的政治社會環境,而或被迫,或主動的去「管政治」。地方與中央民代的定期選舉提供人民參與政治的平台,有些人物崛起,有些人物下台,有些人物引領風潮,有些人物沒於潮流,這種流動使政治不致形成絕對的腐化生態。
當然選舉也不是萬靈丹。有一句很生動的台語,或許有點粗魯,但實在是直率貼切,一針見血,在某些情況下真的無可替換。那句話叫「死好!」,比方在台灣某些地方,一直任由某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家族持續惡搞,爛到根去,但下次選舉,他們還是贏,等他們魚肉地方,中飽自己各種口袋,出大事曝光後,那個地方的選民哀叫說誰來幫幫我們,清理這些事情啊!但是下次選舉,那個政治人物或政治家族又推出「形象清新」,例如貌美年紀輕,或有高學歷之類條件的代理人,結果又當選,繼續惡搞地方。這時候,可能又會聽到各種抱怨,或是求救,或是叫喊要補助,其他地方的人看不過去,也許就會咬牙瞪眼喊一句「死好!」,意思是你讓那個政治人物或政治家族一再一再欺凌你,這結果是你自己找死找來的,怨不得人。這句狠話不僅可放在地方層級的事務上,更可上推到國家層級,未來命運等方面,這是歷經生死滄桑,一次又一次的倒下,不死就爬起,深知你不管政治,政治就會管你的台灣人,幾代淬鍊出的狠話。長年歷史是你不碰政治,政治也不碰你的香港,經過這幾年,應該會發展出屬於香港的獨特精鍊話語吧。
在二二八事件過去三十年後,台灣呼喚著新生代政治,想要推動民主進程。1979年12月10日,爆發了國民黨政府希望壓制住這黨外新生潮流的美麗島事件。緊接著的是12月13日開始的全島大逮捕,隨後在1980年,有八人送軍法審判,三十三人送司法審判。1979年二月成婚的我成為美麗島人的家屬,政治犯的妻子。先生陳忠信是美麗島雜誌的主編,他被判入獄四年,在1983年出獄。
1979年的那個冬天,國民黨政府痛下重手,全台灣噤若寒蟬,不知能否在黑夜中找到出路,也不知夜盡能否天明。我常常全身顫抖,牙關若不咬緊,上下牙就會喀喀喀相擊作響。我工作任編輯的出版社讓我請假幾天,我在同案被捕者家屬周清玉、許榮淑家裡認識更多的被捕者家屬,相聚就有溫度,存在就有力量,即便只是一點點溫暖和些微的力量。
我們一群家屬─ 被捕者的父母妻子和兄弟姊妹,接獲通知說親人被捕後拘押在台北新店、景美交界處的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即迅速聯絡集結,由幾位朋友相伴,帶了衣物等趕去探望。東西送進去了,但是人探望不成。失望離開看守所後,大家走到看守所對面,正在進行工程的馬路邊,徘徊瞻望,不忍離去。這時候,有人說來拍張合照紀念吧,大魏魏廷朝的弟弟,小魏魏廷昱幫著把大家集攏,他大聲說大家振作起來,不要哭,要笑,不要讓抓人的人高興,以為我們一下就很慘的被打倒了。
小魏還說我哥這不是第一次被抓,他這次也一定不會垮,其他人應該也不會,我們在外面也不能垮,不能哭,要笑!
不要讓抓人的人高興。不要讓國民黨得意。在慌亂中,我抓住小魏的話。那時候,我不知道先生會怎麼樣,我該怎麼辦,我不知道還保不保得住我的工作,我根本不敢想要怎麼面對我的父母家人,我抓住小魏這幾句簡單有力的話,像抓住垂下淵井的繩索,努力回到地上站穩。對,我不會讓仇敵高興。往後每一天,我都不會讓仇敵高興。
如果你問我用什麼信念撐過那段日子,我很想說出偉大的信念,高遠的理想,但其實那時候,我顧不得那些,我看不出我站在歷史的哪一個點上,我不知道那是歷史陣痛的前夜,我完全不曉得先生、同伴、台灣會往哪裡去,故友唐文標當時是我們的鄰居,他每天在為歷史要倒退了怎麼辦而痛苦,這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就只是很明確的曉得,我絕對絕對,不要讓仇敵高興得意。讓他們高興,我就輸了。我的戰鬥,這才開始。
這種情況下,第一優先是要活下去。幸好雜誌社讓我繼續工作,我因此有收入,可以維持原來租下的家屋,可以就近照顧獄中的先生。如果失去這份工作,我大概會找找其他雜誌、出版社的工作,但貼在我身上的政治犯家屬標籤,想必會讓我不容易找到工作,那麼,不曉得我夠不夠格去後來一本接一本出現的黨外雜誌工作?當時也曾有朋友找我談過要不要出來選台北市議員?我認為我不適合,因此婉拒了。
我用我比較適合的,變動最小的方式,也是讓我爸媽比較不擔心的方式維繫著生活,即使是這樣,也不輕鬆。母親不在後,我曾在累極的時候給先生寫信抱怨道:「這幾年,我像是把自己剖成了兩半,一半給你,一半給工作。給爸爸的實在不多,剩下來想要留給自己的,好像一些也不剩了。怎麼樣光明的度日,我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但是怎麼樣合理的做人,我得到的分數,應該並不高。不過我能怎麼辦呢?我已經有點兒透支體力了......」
信上寫的,是我當時的苦惱,我想其他的美麗島政治犯家屬應該也有差不多的苦惱。我們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周全。如果累一點,就能把該顧到的都顧到,那心裡也舒坦,但就是做不到把該顧的都顧周全。我那時候最為掛心的是遠在高雄的老爸爸,但我就是沒辦法常回去看他。編務吃緊的時候,曾經元旦都不能放假要加班,平日我星期六要上班,常常還得加晚班,星期天早起做了菜帶去看先生,看了回來若可以不加班,就趕回家做家務事。星期一很快的又來了。我睡得不夠,還曾因此犯了病,幸好年輕,請假看醫生,吃藥,又飽睡幾天,算恢復得快。
我過得像個打轉的陀螺,稍停一下,就能立刻睡著,睡醒還能立刻又轉,這便已經覺得自己很不錯了。我很少想到自己,似乎是能維持著在極限內打轉不倒就是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而且我每天還能抽空看幾頁書,偶爾能與朋友吃頓飯,看場電影或表演,有一次在看俄國芭蕾舞團演出時竟然不支睡著,即便是這樣,那短暫的坐在劇院裡的時光也是自由、美好的時光,獄中的人渴望而不可得的。因此我在想到爸爸難過的時候,給先生寫信抱怨說我都沒給自己留些什麼,其實也不全對,夏天植物園的荷花,我不是在採訪途經時順便好好的看了?最先是唐文標借我的金庸武俠小說,我不也一本一本都看了?在美國的一位好朋友曾說世界上該看、好看的書太多了,所以她決不碰金庸。也對,但既然金庸到手,怎能不打開來看,而且第一本上手的《書劍恩仇錄》一看就看到紅花會四當家文泰來遭清廷追捕被擒,妻子駱冰與紅花會眾英雄極力營救的情節,竟與現實世界有相通之處!
其他諸事,也多有會通,抱怨或開心,可寫的都一一寫在寄到獄中的書信裡,像那夏日荷花,即很美的以文字寫生,寄了給先生。我很少想到自己,我只是看著眼前的世界。
也有許多事情沒法寫給先生,或只能淡淡一筆帶過,例如他被帶走以後,我在外面遇見了哪些黨外的或同情我們的朋友,朋友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都不方便寫。
先生被帶走的當天早晨,我很快接到黨外朋友蘇慶黎的電話,指引我去景美陳鼓應太太家,由此而與其他被捕人犯的家屬碰面認識。一天不落,大家就接上線了。家屬裡面最有活動力的是張俊宏太太許榮淑,她家和當時抱病的姚嘉文太太周清玉的家,及景美陳太太湯鳳娥家,是我們最常去的據點。
隨時有人跟蹤的家屬和關心家屬的黨外朋友能有些個方便可去的聚會點很重要,去那裡,可以聯絡事情,放心講話,也可以放心哭泣,暫卸壓力,不用擔心讓外人側目或家人心傷。在那裡,大家很自然的承擔起自己可以做的事。像曾在新店大坪林的天主教女子公寓專任管理職十多年的黨外朋友袁嬿嬿那時常去許榮淑家,她一去稍坐一下,也不多說,常常就微笑牽起許榮淑的小女兒說走,我們出去逛逛。逛了半天,她可能帶著小女孩去公園玩過,請她吃了好吃的,或還給她買了新衣服,兩人才笑嘻嘻的回來。她做的這些都是突遭巨大家變,無法理解,不知所措,關在家裡的小女孩,需要媽媽為她做,但媽媽實在沒空為她做的事。當時沒有小孩的我,看看而已,無心理會小孩的事,後來自己有了小孩,才想起,才應證小孩的需要十分巨大,要滿足他們生活、心理林林總總的需要,所花心力難描難畫不簡單。我也才理解袁嬿嬿當時一派輕鬆,那麼自然的牽起小女孩的手說來,我們出去玩,對任何一個在那種心力交瘁處境下的媽媽都是莫大的幫助,她真是一個暖心腸又行事細膩的人。
我後來常說美麗島事件的家屬是台灣歷史上待遇最好的政治犯家屬,我們得到來自海內外許多人的關切,台灣走到七零、八零年代的分水嶺時,有更多的民眾勇於站出來追求理想,支持民主運動,有更多的人看到政治犯家屬不會別過頭去,裝作不看見。美麗島事件後第一個舊曆年來了,我回彰化田尾的先生家過年,然後初二要回高雄的娘家。在田尾家裡,婆婆什麼事都不要我做,每個人都待我好,不多說什麼,只叫我要多休息。大家在像會客室的大灶間忙著水火諸事時,一位在外地農園種水果的舅舅來了,他一看到我就溫和的對我笑,然後走幾步過來正眼看著我,說:噢,新娘~
剛剛還很平靜的我,立刻眼淚水上湧,因為感應到他對我的同情、憐惜與了解。
那麼簡短的語言,卻能傳達那麼多素樸率直的東西。事件發生後一直努力撐持著不散架的我,攔不住隨內心泉湧的感激而落下的淚水。沒有什麼是比同情更好的支持。
我想,安靜種水果的舅舅,還有台灣許多在舅舅年紀上下的長輩,記憶裡多少深藏著經過、看過、聽過的政治事件如二二八的血淚剪影,眾多無畏的美麗島人的表現引發出他們夾帶在回憶裡的感傷、恐懼、不滿和憤怒,他們投射在美麗島家屬身上的是無比純粹的同情共感的浪潮。因此後來他們用高票將出來參選的美麗島家屬和辯護律師送上政壇,連帶著大力放送的是他們要改善現狀,要正視過去的期望。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當年年底,旅美作家陳若曦親帶一份由二十七位旅居美國的著名學者和作家余英時、許倬雲、林毓生、張灝、楊牧、白先勇、許達然、李歐梵......等人連署的信件回台,請求政府當局不要以軍法審判美麗島案。陳若曦在台灣兩度見到蔣經國總統,充分轉達了這些作家、學者的意見,她還犯顏直陳12月10號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這件事給我們家屬很大的支持與安慰,深感江湖路險,卻並不孤單。我們並未看到那份意見書的內容及全部連署人名單,但從先後曝光的部分人士可知那是份不分黨派的重量級名單。
名單中有位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思想史專家林毓生教授,我未見過林先生,但知道先生陳忠信與他有段結識的特殊淵源。林先生於1976年有篇以英文發表的研究專文〈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 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含混性的實例〉,當時年輕的陳弱水先生和陳忠信看到後,因為覺得好而分別自行翻譯為中文,並都郵寄給林先生。林先生收到後認真校改兩篇譯文,中文版的文章發表於1980年的〈時報雜誌〉,後收入《思想與人物》一書。
陳忠信在翻譯那篇文章前,曾在東海大學聽過林先生演講,也在反應熱烈的演講會後向林先生討教。譯文寄給林先生後,他與林先生多次信件往來,承林先生認真解惑。這些我略知一二,也十分感激林先生積極救援美麗島人。1980年秋,九月,我在報上看到林先生在台北,且將於南海路植物園區的國立台灣藝術館演講,講題是「中國人文的重建」,當即覺得我應該替陳忠信去聽這場他本人如果自由在外的話一定會去聽的演講,有機會的話,我也很想當面謝謝林先生。
我與黨外的朋友,作家曾心儀一同去聽林先生的演講。全場滿座,大概擠了一千多人吧,幸好我們早些去,找到了座位。林先生的演講風格是不慌不忙,不疾不徐的,時或吐出幽默的語句,引得全場大笑,他又因為努力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事情講清楚,實在不可能了,他就會苦惱的搔頭說「anyway,這是很複雜的,現在沒辦法多說」,而又引得聽眾會心大笑。連同演講後的提問時間,整場演講大約長達三小時,完全沒有冷場,大家一直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一個字都不想漏掉。
散會了,演講的舞台上仍有不少聽者圍在林先生身邊求教。我和曾心儀也走上舞台,站在人圈外。到人群稍微散了一些的時候,曾心儀斷然走上前,輕輕跟林先生講了幾句話,林先生立即轉頭看向我,並朝我走來,噢噢,他握住我的手說,你們好嗎?忠信好嗎?
他又轉首朝斜後方看,招手要一位優雅的,著藍色衣裙的女士過來,那是林師母宋祖錦女士。我簡單向他們報告忠信大概會定案坐四年牢,但是他很好,我們都沒有問題,請放心,我也代忠信謝謝他們關照。
一個月後,陳忠信的案子定了,他由土城看守所發監桃園的龜山監獄。
陳忠信出獄後,有機會去美國看了些朋友,也曾到威斯康辛拜訪林先生和林師母。而他們兩位若來台灣,每回都會相約見面,談林先生的思索研究,談台灣的情形,談世局的發展,
笑談縱論後,耿直的林先生常常說中國是最壞的人在最高的位置上,就這麼回事,一群王八蛋,你說怎麼辦?那台灣又是怎麼回事?忠信你說說!
這兩年,林先生身體不好,不方便遠行,我們長久沒見了,有時候陳忠信想起會學以前林先生說什麼的語氣,學得好像好好笑,笑完我們掐指算那是哪一年啊,噢噢原來有那麼久了。回溯過往,原來林先生、林師母關照我們那麼久了。
那段我與美麗島家屬和親長、朋友共度的過往,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這些年,我斷斷續續寫下相關的回憶,以及零零星星的其他事情,竟以美麗島為名,成書二冊。成書的方式有點像我把東西擺在那兒,讓編輯來挑,挑中以後,隨編輯依其旨趣排列組合,讓我這作者都會驚嘆:這真成了書了!有時候編輯挑東西,我也會自賣自誇出主意說這篇怎麼樣?那篇好像還可以?不選會不會有點可惜?不過我亦曉得我主觀太強,可能會干擾人家選物,稍稍說說而已。我希望,對於欠缺台灣經驗的香港朋友,我的書可以是種誠懇的陳述:在台灣,有個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父母來自上海的普通女子,在很年輕的時候,撞上政治大轉折的年代,她和她身邊的人遭遇了什麼事,他們又如何對應,她和她的時代的故事還正在進行,發展的端倪,可能寫在現在,可能藏於過去......
香港現在也正處於大變局的年代,報社被封,媒體被斷,說話的人被抓,整個社會在打亂、重組,重組後的新局是不忍去想像的,香港,現在也是產生政治犯和政治犯家屬的地方,暴力式的震盪才正開始在家屬們的內心翻攪。回想四十多年前我們美麗島家屬的處境,那是個多層次的結構,結構的核心是政治犯,我們家屬環繞在其外圍,在我們的外圍是關心、照顧、同情、支助,並提供希望的,通連海內外的綿密網絡,我們努力支撐著政治犯家人,我們外圍的綿密網絡用力支撐著我們,大家是一個整體,這樣走過風雨途程。任一環節如果鬆動,就會有程度不一的影響。如果當時的美麗島家屬沒有外圍的支撐網絡,想必活下去的處境會更艱辛,看不見未來,也無法突破出擊。幸好當時的我們是一個保有願景的,相互連結的整體,即便無能如我,沒有走上政治舞台如我,也有心念如此:我要笑著活,決不讓仇敵得意高興,也決不忘記仇敵做了什麼。
但是,香港的情況與當時的台灣很不一樣,我只能述說我們美麗島家屬的一些經驗,而無法提供香港的政治犯家屬太多建議。香港政治犯家屬的對照組大概不在台灣,在中國。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家屬團體是六四之後的「天安門母親」,她們平日偶有聚會,相互打氣,年年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遞交一份請願書,要求真相、補償和問責,從未接獲回應。母親們年事日高,漸漸凋零,今年是六四的三十二週年,看報導,去北京市郊公墓奠祭的只有「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張先玲女士和六位成員。我想北京政府在等待她們退場。唯物主義的政權認為人死燈滅沒戲唱,她們將失望以終,一切就被掩蓋、遺忘。
作為人類,天安門母親不一定活得比極權政府長,作為母親,天安門母親承受的太過太重,她們承受的不只是喪子之痛,還有整個國家的遺忘與冷漠,許多人認為她們多事,事情過去那麼久了,好好低頭過日子不行嗎?做什麼要挖瘡疤,讓人難受,給國家添麻煩?這樣想的有許多是天安門死難者的兄弟家人,甚或父母。國不國,人不人的悲愴,全壓在張先玲、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身上。
香港的政治犯家屬必須要了解處境相近的天安門母親所受之苦,同時也請了解她們不屈、不忘,承受苦難的身影已成超越性的典範,有一天可能會是那個國家的國民要從歷史中挖出來珍藏的精神遺產。
但那可能是多年以後的事。在那之前,不能碰政治的受難倖存者和他們的家屬能夠做些什麼?在社會生活的政治以外領域,香港的公民是否有什麼可以做的事?即使是很細微的事,但或許可以匯成涓涓細流,在這涓涓細流中承載著、延續著人的精神?
蘋果日報被查抄停刊,今年的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以後,我看到一則新聞講有位蘋果的員工擔心留在大樓內的幾十盆虎尾蘭、黃金葛和蕨類、芋類等植物無人照顧會乾死被棄,就與大樓相關人士聯繫後,貼文公告將擇日把所有植物搬到大樓門外,歡迎對植物有興趣的朋友自行搬回家照養。是日,27日,果然有許多市民一早即在蘋果大樓外排隊等候領養,所有植物很快悉數領養完畢,還有人向隅沒領養到,那位熱心貼文的員工忙剪下一段段黃金葛枝條,分送給人說枝條帶回去,插養在水裡、土裡都好活,還可以繼續分枝。此外,原本飼養在蘋果大樓內的一些鳥雀,也被義工帶走,且按照牠們的物種屬性,適當的照顧牠們。
這真是我近期看到的最最溫暖,最為扣人心弦的新聞訊息,香港人如此愛惜動植物,當然反映了他們愛屋及烏的心理,另外也顯現了他們具備一流的公民素質,最美好的人的精神,難怪香港人不論老、中、青,近年來在政治活動上表現耀眼,震動國際,當時代既倒於眼前時,他們,已不再是唐文標所說的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族群。
我敬愛的香港人,會找到出路的。那也許是一條遠路,在機場異國,拖著行李奔跑,或是在自己家的窗邊,給一盆黃金葛澆水。然而,「遠路不須愁日暮」,懷揣著走遠路的心理預備,日暮,日出,一日日走下去,看會走到哪裡,看會走出什麼。這一段歷史,可能是創世紀的,可能是劃時代的,很難在前人的經驗史裡找到可與相比並論的。我覺得我不能告訴香港人太多有用的經驗,而是有一天,香港人會告訴我,告訴我們台灣人,他們尋找出路的歷程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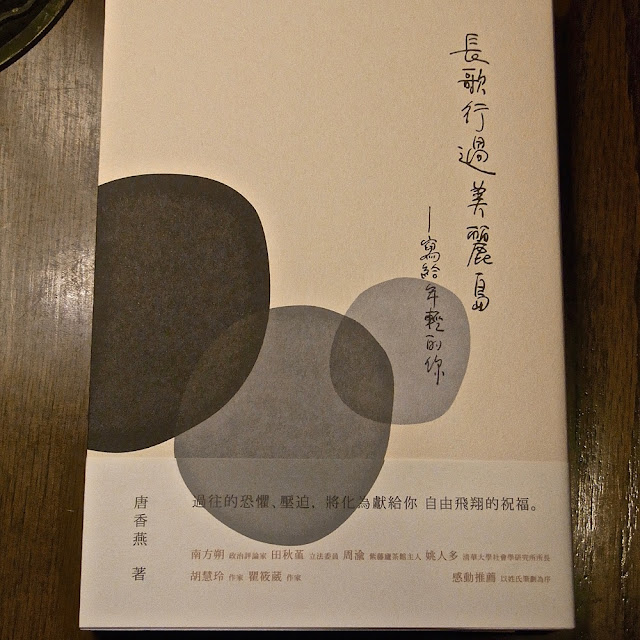


















4 意見:
讀著讀著,好想哭~~~
我是看到香港人的事情掉眼淚~
謝謝。
謝謝你~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