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喜歡看我寫人~
因為有故事吧,我想。
朋友又說了:你寫的人,好像都不在,都走了,是因為他們不在了,你才寫的嗎?
我的立即反應是:嗯?我也寫了一些還在的人啊,我覺得也還可以看啊。
接著我又往下想,朋友會有那種我寫的人,好像都不在了的印象,會不會是因為她喜歡的,收在書裡的那幾篇,剛好都是講已經不在的人:唐文標,蘇慶黎和蘇媽媽,還有吳美雲......? 而那幾篇也是比較多人會提到或喜歡的,說是因為好像看到他們在眼前活動或講話。也有人說,是因為好像看到他們活動、講話的那個時候,那段時光,聽到時代轟隆隆的響。
向過去,我惓惓致意,感謝有人殷殷回應。
最近看到以二十多部諜戰小說構築出一個複雜、幽微世界的勒卡雷在他的回憶錄《此生如鴿》的自序裡說:「真的有『純粹』的回憶這種東西嗎?我很懷疑。......但是請放心:我絕對沒有刻意偽造扭曲任何事件或故事。必要時會略作掩飾沒錯,但偽造扭曲,絕對不必。只要回憶裡有任何不確定之處,我都會特別述明。」
勒卡雷所述,應該是一個作家的基本修為。或許也因為擁有那些雖然很難百分之百把握,但確實留存腦海的記憶,他後面說的兩句話才能成立吧。他在後頭這樣說:「有些事情我在當時並不瞭解其中的重要性,後來很可能因為某位主角的離世才意識到。」
有些話語,有些影像,在過去以後並未沈落,反而慢慢浮現,於是意識到其重要性。聆聽,凝望,有時微笑,有時落淚。隔著時光閃動的距離,我試著描摹那些話語和影像,還有氣氛。
有些人物,有些事情,年輕的時候是抓不住的,因為人事正在進行,或者經驗還未成形。前兩年撰寫一文叫〈雲端猜想〉,提到故友孟祥森在〈殷海光的最後夜晚〉文中描述的陳雲端,那個晚上是殷海光教授故去前一晚,年輕的哲學系學生孟祥森在台大醫院的病房為老師守夜,夜深時,他看到寂靜長廊的那一頭有一女郎獨自行來,走近方知是沒見過殷海光,但特意來看望殷海光的陳雲端。
孟祥森文章寫得好,不用贅語,如實刻劃,真摯感人。但我自己曾於台大醫院病室陪伴友人過夜的經驗,在閱讀孟祥森文章之時同步顯影,我看到古老病院入夜後昏暗的燈光,在深沈的寂靜中,我聽到長廊上偶而傳來的橐橐步履聲......我的實際經驗也助我進入孟祥森描述的那個夜晚,走近陳雲端,觸及她的性格。後來我自己憑藉一些親歷或聽說的情境,猜想、織寫陳雲端,她在殷海光的最後一晚,走到他的病床邊,幫著孟祥森照顧將逝的老師,當然是我會採集的畫面。
經驗與記憶使得理解與共情是可能的。當你覺得可能的時候,或許才好下筆。
嗯嗯,朋友抓著我不放說,雲端也是已經不在的人,所以我剛才說的沒錯吧?
好吧,我說,寫她的那篇文章,確實是因為她不在了才會寫,要是她還在,我就不會寫那猜想文,因為心裡會想或許哪天我能近身接觸她,釐清我的種種猜想也說不定?是生死距離,是失落感讓我寫出來的,與她沒有深交,也沒有機會與她親近,但就是對她有一層一層的感覺,逐年堆疊,放在心裡,像木頭的年輪層一樣。所以,只能猜想了,我明言我是猜想。
然而也不是有生死距離就能夠寫,也有過去的人經歷了非常打動我的事情,我想了想,沒動筆。放一放,到我九十、一百的時候,再來寫吧。那時候,我隨心所欲,沒人能說我老太太什麼了!
由此想到我最近讀的另一本回憶錄,六四後流亡美國的作家蘇曉康寫的《離魂歷劫自序》。1993年,蘇曉康一家三人在美國高速公路上出大車禍,他與兒子幸能康復,妻子傅莉卻顱內出血,內臟撕裂,魂魄出離,無法言語和行動,幾幾乎不能回返人世,接受正規和另類各種療法兩年後,方勉強出院回家。蘇曉康以這一段艱苦的血淚歷程為中心,往回寫與傅莉結緣,建立家庭的經過,至1989年遭遇六四的磨難,一家三口分隔兩地,兩年後才得於美國團圓。他又往後寫與過去斷裂的移民要在新天地紮下根苗之萬般不易,遭橫禍後更需付出非凡的努力,且幸得來自各方的援助,一家人才不致滅頂,但拼命活下來以後,身心都不是原來的樣子,「生命的涵義徹底改變」,兒子也提早結束童年......
這一家人驚濤駭浪中險淪波臣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國時報的副刊看過蘇曉康於專欄裡寫,但我看的多有跳失,並不連續,現在找1997年將專欄諸篇補綴結成的書重讀,方完整的隨著經歷一遍,不敢說是感同身受,但實在是感慨很深。作者在「後記」自述,他是在傷痛中渾渾噩噩由最初的零散筆記寫成這本書,直通通把自己、傅莉和兒子在大難中的種種慘狀、失態端了出去,這算不算是侵犯家人的隱私?將來兒子成人後,或傅莉完全清醒後,能夠接受他這樣寫他們嗎?此外,寫一家的私事,也免不了涉及旁人,寫當時的情境,不免也會旁及遠遠近近的人與事,他曾考慮要剪裁、篩選,「可是許多人和事,都同我們的絕望連筋拽肉的絞成一團,我是想摘也摘不乾淨的,索性和盤托出。」
在實際的生活裡,最好能適當保持我們與人的距離,不過下筆為文,要如何適當保持我們與人的距離?這是很多散文或小說作者會面臨的問題。我們的觀點,可能是被寫者所不樂見的,我們的寫法,可能是被寫者所不同意的。寫了,可能惹人不快,被責越界,自找麻煩。
回到勒卡雷,他的回憶錄《此生如鴿》以不短的篇幅寫他的父親和母親,那兩位,真的不是我們會希望有的父親和母親,不過,成熟的作家八十多歲了,有能力回望在他早年,在長廊的那一頭,他所看見的父親和母親,不論他們是怎麼樣的人,他沒有為長者諱,一筆一筆記下。他說:
我花了很長的工夫才有辦法動手寫羅尼。他是騙子、夢想家、偶爾坐牢的囚犯,也是我的父親。............他對危機有癮頭,對表演有癮頭,是厚顏無恥、口若懸河的佈道家,是非搶盡鋒頭不甘心的人。他是個充滿妄想的巫師,是個自詡為上帝金童的說服者,毀了許多人的生活。
那生活被毀的許多人,也包括勒卡雷年輕的母親,她在勒卡雷五歲,勒卡雷的哥哥七歲的時候,悄悄拋下孩子,逃離丈夫,離家出走。勒卡雷二十一歲時找到母親,在車站月台很尷尬的見了面。他為了要不要擁抱母親,要怎麼擁抱母親,糾結了許久。那中空的十幾年很難彌補,他始終說不上來在他的成長年代缺席的母親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是他發現「母親為自己─也為我─創造了詩情畫意的母子關係,從我出生延續至今,不曾間斷。」
他們,父親和母親,在他筆下,栩栩如生,進入文學殿堂。不過他很小心的把關於父母的篇章放在書快結尾之處,因為要是放在書開頭的地方,他怕他的父親即便死了,仍有驚人的力量會重施故技,跳出來操縱他,操縱全書。那個當年被父親逼著去向人討回一筆巨款,討不成,人家反而說欠款的是他父親的十六歲迷惘少年,長大終於有辦法應付可怕的父親了。
總之,如果你能寫得到達勒卡雷的高度,你就有權寫你想寫的。也就是說,只要能達到文學的高度,你什麼都可以寫。文學女神的標準,比你的父母親故嚴苛、無情。如果你得不到文學女神的認可,父母親故要責備你,鄙視你,冷待你,也就只好低頭認了吧。
後記:
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1997年由時報文化出版。我借看的是這個版本。2012年印刻出版又出此書增訂版,閱讀增訂版的相關介紹,很高興知道傅莉將這書翻來覆去不知讀了多少遍,讀完又常把書送給朋友,蘇曉康說「她在讀她自己,她在一次失去記憶的恐怖之後,重新找回自己、找回兒子,無數次的失聲痛哭,掩卷欷歔,無數次的誇我:怎麼從來不知道你能寫東西?」我覺得傅莉的痛哭與歎賞也是對其他作者的鼓勵,對文字的讚美,和對文學的期望。
英國小說家約翰‧勒卡雷(1931~2020)的回憶錄《此生如鴿》,THE PIGEON TUNNEL ─ Stories from My Life,寫一個一個人的一樁一樁事,如群星閃耀在他人生的天幕上,中文版在2017年由木馬文化出版,譯者為李靜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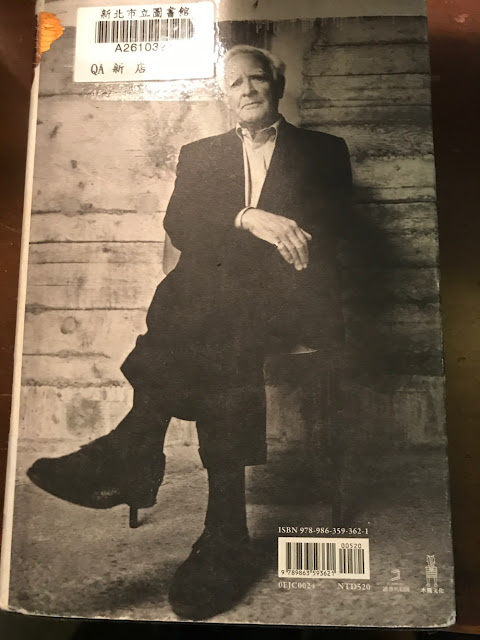















2 意見:
感動,大師級成就。
謝謝,推薦你去買我提到的書─忠信說我貼出的書影好舊,不好看,但我從小在圖書館找書看,習慣了那種舊~
張貼留言